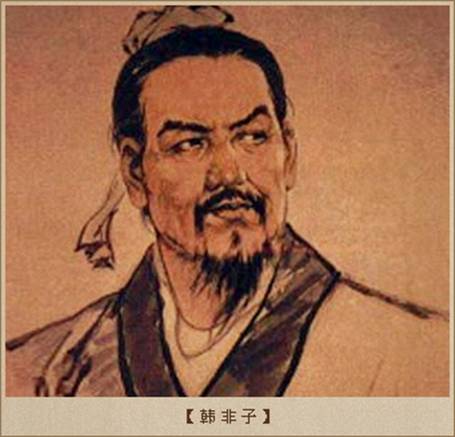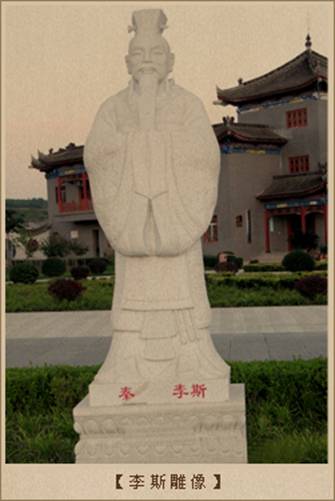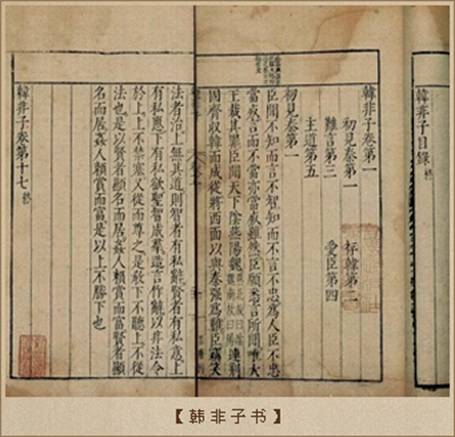千古帝师——韩非子与法家思想的形成
在中国整个封建君主时代,一直就存在着两个圣人。一位是显性的圣人,就是人们熟悉的孔子。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被历代君主捧得很高很高,受到后人的顶礼膜拜;另一位则是隐性的“圣人”,就是不太为人所知的韩非子。他为封建统治者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策略,其思想理论虽不被视作正统,却往往受到帝王们的青睐,将其运用到安邦定国的实践之中。他的地位虽不及孔子显赫张扬,却得到了历代帝王内心深处的拥戴。
事实上,韩非子虽然学识深厚、文才飞扬,但其一生却是落魄失意,最后含冤而去。他生前怀才不遇,为什么他的主张在死后却能发扬光大,他的思想渊源何在,有何创新?却为何让历代帝王暗自揣摩却又不敢明言呢?
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法家曾经风光无限,威名远扬。与被诸侯国君主敬而远之的儒家 “孔孟之道”, 和“无为而治”孤芳自赏的道家相比,法家是先秦时期最受诸侯国君青睐的学派,也是最具有实力的学派。从魏文候重用李悝变法,使魏国独霸中原近百年开始,法家一直是最受器重的“显学”。其后吴起、申不害、商鞅,都曾经取得最高统治者的信任,都雷厉风行的实行变法,都取得令人侧目的成就。法家成为当时的显学,法家思想成为众多国君驾驭群臣,统治臣民的最有效的手段。
然而,最终使法家思想成为帝王统治权术的却是韩非子和李斯。韩非子大约出生在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33年。他是战国末期韩国的公子,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李斯也大约出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08年,楚国上蔡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人,他是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也是法家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有趣的是,韩非子和李斯都是思想家荀况的学生,而荀况本身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人物,但荀况并不排斥法家,他主张礼法并用实现国家的统一。而韩非子和李斯则全面转向法家。
韩非子和李斯追随荀子的时间可能大致相当,彼此也较为熟悉。李斯学业有成之后,看到东方六国已经衰落,决定去秦国开创自己的事业。相传当李斯离开荀子时,师生已经有了较大分歧,荀子主张依靠礼法治国,君主也要推崇礼,尊重贤人,注重教化;而李斯则认为,君主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无所谓是非,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公元前247年,李斯来到秦国,此时秦庄襄王刚刚死去,尚未成年的嬴政继位,秦国军政大权全掌握在相国吕不韦手中,李斯作了吕不韦的门客,很快成为他的心腹,从而有机会接近秦王。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以法制国”成为立国之本,富于心计的李斯很快就看到秦王才是自己长久的依靠。于是,他根据历代秦王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志向,给秦王写了《论统一书》,劝说秦王抓住机遇,实现“天下一统”,既投其所好,又显示了自己的才学。因此,李斯很快受到嬴政赏识,先被任命为长史,后又拜为客卿,成为秦王的左右手。公元前237年,嬴政刚刚亲政,秦国就因为韩国水工郑国在秦搞间谍活动,发生了驱逐六国客卿的事件,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为了能够留在秦国创建一番功绩,李斯又写了《谏逐客书》,用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正是因为有了客卿的辅佐,才推动了秦国的进步,最终使秦王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也因祸得福,从此青云直上。
就在李斯于秦国春风得意的时候,韩非子却是郁郁寡欢。作为韩国的贵族,韩非子当然想依靠与韩王的血缘关系获得韩王的信任,然后凭借自己的才学,实现富国强兵,与各国一较高下的宏图伟业。然而,他自己却天生口吃,以致在交流时往往词不达意。在战国盛行依靠言语来说服君王的时代,韩非子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说客。而韩国从秦商鞅变法强大以后,与秦国交战,基本上就没有取得过胜利,已经完全丧失了与秦对抗的勇气。面对秦国的步步进逼,昏庸无能的韩王居然将当时的水利专家郑国派到秦国,让其唆使秦王修建郑国渠,试图以此消耗秦国实力。这个看似疲秦的阴谋最终敲响了韩国灭亡的丧钟,而沮丧的韩非子也只能是以著书立说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展示自己的才学。
韩非子的思想实际上是对战国以来历代法家思想的一次大总结。他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道的“势”,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创新,最终创建了新的法家学说,为君主及后世帝王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兼治的专制论,这就是为古人所称道的“帝王之学”。具体说来,韩非所说的法,是一种法律条令。韩非子主张,任何事情都要通过法律加以规定,法作为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落到实处就是罚与赏。他强调要厚赏重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要做到“轻罪重刑”,从而达到“轻者不至,重者不来”的治理效果。韩非所讲的术,是君主对臣下的统治手段,是藏于君主胸中的心计,他煞费苦心地考察与研究了奸臣的各种行径,并给君主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防治手段。他归纳出“八经”、“八奸”、“备内”、“三守”、“用人”、“南面”等一系列政治权谋,目光从层层官吏一直扫射到帝王后妃、夫人、嫡子。其大胆、犀利、露骨的分析,无不令人惊叹。他所创立的权术,其中有很多都是非常卑鄙肮脏的,是可以心领神会却又不能明言的,但韩非子却毫不顾忌地深入研讨,并进行赤裸裸地描述。韩非所说的势,就是君主的权威,就是生杀予夺的权力。法和术实施的前提是大权在握,法和术实施的结果是大权握得更紧。
韩非子是个君权至上主义者。他提倡尊君,主张君主集权、专制。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认为君权集中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法家思想,激烈批判了法家以外的其他学说,特别是当时流行的儒家和墨家。他主张严格限制言论与思想,禁止私人著作流传和讲学,只准学习国家颁布的法律。并为君主精心设计了一套法、术、势结合的统治权谋。综观其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国古代各种学术思想的实际政治效应和操作手段实在没有超过韩非的。
韩非子的思想是对战国时历代法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精华。因此,他的主张虽不能引起韩王的兴趣,但当雄心勃勃,一心想统一天下完成霸业的嬴政,无意中读到了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时,便深感正中下怀,大为钦佩,感叹说如果能见到作者并与他相处,则死而无憾!而李斯投其所好,声称韩非子是自己的同学,可以用韩国水工郑国事件为借口,逼韩非子来秦国。于是,嬴政派兵攻打韩国,并指定要韩非子赴秦解决两国纠纷。结果如其所愿,韩非子以国家百姓为重,亲赴秦国。
秦王嬴政见到韩非,高兴万分。而李斯则意识到同学的到来,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很可能好不容易到手的荣华富贵即将毁于一旦。于是,李斯趁秦王没有全面起用韩非之前,就和姚贾二人诋毁韩非,说韩非子作为韩国的贵族,不会真心实意帮助秦国。对郑国事件还心有余悸的嬴政听信了谣言,很快将韩非下狱,李斯为了彻底解决这位潜在的对手,便给自己的同学送上了一杯毒酒。于是,当时最杰出的法家思想家就此命丧黄泉。当醒悟过来的秦王派人去赦免韩非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嬴政、李斯将韩非理论作为治国方略,付诸实践。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多次派人携带大量的财物,贿赂六国的君臣,离散各国间的关系;对六国的人才,能收买就收买。秦统一六国后,嬴政改秦王为秦始皇,改“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朕”,建立一套完整的封建帝王制度。在政治统治上,李斯与秦始皇彻底废除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大小各级官吏大多由帝王直接任免,加强君主权力。在中央设三公九卿,分别负责国家大事,建立了一整套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在法律制度方面,严格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做到各个方面都有法律制度的约束。为了控制思想,甚至不惜“焚书坑儒”。所有这些措施,都可以从韩非子的理论中找到依据。
到汉朝以后,“汉承秦制”,对秦朝的大部分制度完全继承。虽然汉初“黄老思想”曾一度成为国家指导思想,汉武帝确立儒家的统治地位,但汉朝统治者骨子里采纳的还是法家理论。而韩非子讲述的“权谋法术”更是被历代统治者发挥得淋漓尽致,但越是阴谋用尽,就越要推崇孔孟之道,以“德”“礼”来装点面门。
所以说,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不仅主宰了秦朝,而且实际上也主宰了从秦至清的整个封建时代。法家思想和法家的权谋才是历代帝王心领神会的治国御下之术,因此,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中,他们一直扮演着帝王之师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