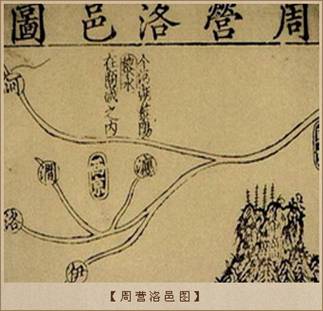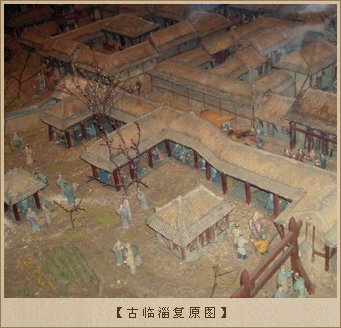国之重镇——先秦时期城市的兴起
1928年的秋天,河南安阳,为了寻找带字的甲骨,中国考古人员开始了对殷墟的发掘工作。由此开始,一座几千年前的城市开始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伴随而来的疑问是,中国的城市起源于何时?又是如何发展变迁的呢?
一个是摩肩接踵、挥汗成雨的昌盛之都,一个是让人三致千金、富甲四方的“天下之中”,它们的繁荣源自哪里,与商业的发展有何关系?在那个风雷激荡、群雄并起的时代,城市的兴盛与统治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远古时代的中国境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和部落。部落间不断的战争,使得人们为了部落的安全修建防御性设施,传说“黄帝筑城,造五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这种设施是城市最原始的萌芽形式。随着阶级分化,国家产生,工商业和农业分离,脱离生产劳动的统治者和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成员一般居住在城堡中,城堡具有了政治、经济、军事的功能。那么,中国最早有史可考的城市源于何时呢?
对我国早期城市历史有可靠记载的是周朝。周王朝开始于公元前11世纪,由于周朝灭商后,都城西迁,建都丰京、镐京,在今陕西西安附近,两京仅隔一河,中间有桥相连接。《周礼·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轫。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是中国最早的城制记载。大意是说,镐京方圆九里,每边有三个门,九条街道纵横,前堂是朝堂,后面为街市。王公贵族和手工工匠居住在城中,经济自主性较弱,几乎完全依靠周边农村的各种供应。由此可见,最初的城市和商业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商业的发展开始促进城市的发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商周之时,工商业都由官府垄断。春秋后期,开始出现了独立的工商业者。战国时的手工业者已经分工很细,有冶金工、陶工、木工、车工、皮革工等。由于社会分工,手工业者要 “以械器易粟”、农民要“以粟易械器”,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大小地主剥削来的农产品,也要通过商人换取奢侈品。这些行为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于是商业和城市也开始兴盛起来。
春秋时候,大都市不多。一般国家的国都周围不过九百丈、卿大夫的都邑只有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九分之一。战国时期,由于农工商业的发展,不但城市增多,而且人口也不断增加,规模也大大扩大了。有些大城市周围不止三里,户口也不止万家。《战国策·赵策三》记载赵国名将赵奢对当时城市发展规模的古今对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可见,到战国时期,城市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急剧膨胀,这首先表现在各国都城的繁盛。
在各国国都中,齐都临淄首屈一指,规模最大,也最繁华。临淄不仅是齐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文化中心。战国时期,临淄居民多达7万余户,家家富足殷实。《史记·苏秦列传》有这样一段为人熟知的论述:临淄城有七万户人家,以每户三个成年男子计算,就有二十一万男丁,不必征发其他郡县的男丁,临淄就可以组成一支二十一万人的大军。临淄的街道车马往来拥挤,车的轮轴常常相互碰撞,行人肩擦肩。人们的衣襟连起来可以合成围帐,人们的衣袖连起来可以合成幕,大家一挥汗就好像下雨一般。在当时的临淄城内,论经济则百工兴业,商贸繁荣,丝帛鱼盐,汇聚如山;论文化则稷下学宫,百家争鸣,诸子著述,昭显于世。商业兴盛,人们生活富足;学术繁荣,精神生活提高,这些进一步推动了文体活动的发展。临淄城内的文体活动不仅包罗万象,而且推陈出新。《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载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据说孔子在齐都闻《韶乐》,竟然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可见齐国文艺活动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同样是都城的楚国郢,城墙周长三十余里,街道上交通拥挤,也经常是车碰车、人挤人。据说行人早晨穿的新衣服,到晚上就已被挤破。这虽然属于夸张之词,但也反映了大城市繁华的景象。
如果说,各国的国都因为其特殊的政治影响力而繁荣昌盛不足为奇的话。同样有很多城市完全是因为位于交通中心,成为工商业中心、物资集散地而繁盛起来的。陶就是这种城市的典型代表。
陶在今山东定陶附近,春秋为曹地,默默无闻。春秋末年,陶忽然成为繁荣的都会,陶朱公在陶安家立业,就是因为“陶为天下之中”,在此地三致千金。后人研究认为,春秋时吴国开掘了邗沟及鸿沟,使江、淮、济、泗几条河流可以联络交通。陶位于这一新水道网的枢纽,又加上济泗之间、西至黄河平原都是古代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所以陶占尽地利。鸿沟的开凿,更使陶居于济、汝、淮、泗水道网的中央,就近而言,西边挨着韩魏,东边连接齐鲁;就远而言,又可以从水道到达江淮,良好的地理位置,使陶成为天下诸侯权贵垂涎三尺的宝地。
城市的兴起,经济文化活动的繁荣,与当时颇有远见的各国统治者的扶植是分不开的。西周初年,太公姜尚被封到营丘。针对齐国盐碱地多,人口少的特点,他鼓励妇女从事纺织业,同时发展渔盐,致使“齐冠带衣履天下”。到齐桓公时,管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全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实行专业分工,工商乡专门从事工商业。管仲的改革使齐桓公得以称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延续到战国时期,齐国的强盛富庶更为天下公认。
正是由于工商业的发达,统治者的爱好鼓励,才使临淄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在当时的中原大国晋国,晋文公鼓励发展商业;位于中原中心的郑国,统治者从立国之初,就和商人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意思是说,商人不背叛统治者,当权者也不能对商人强买强卖。于是出现了秦国偷袭郑国,商人弦高以十二头牛假意犒劳秦军,使秦军偷袭不成反而全军覆没的故事。甚至到春秋末期,郑国依附于晋国的时候,晋国使者韩起想要求当时郑国的执政子产帮助他低价购买一只玉环,却被严词拒绝。即便是在商鞅变法中,公然提倡“重农抑商”的秦国,仍然需要各国商人输入大量物质以供统治者挥霍享受。曾经一度控制秦国军政大权的相国吕不韦自身就是一个大商人。
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刺激了货币的流通。战国的货币是从春秋后期开始出现的金属铸币发展而来的,适应了商业发展的需要,战国的货币流通量更大。这一时期的货币可分两大类,一类是铜币,另一类是金币。铜币从形状上可以分为四种:刀币流通于燕、齐等国;布币流通于韩、赵、魏等国;圜钱流通于周、秦;形状像贝壳的蚁鼻钱流通于楚国。楚还铸有一种称“郢爰”的方形金币,上印“郢爰”二字,后人称为“金饼”或“印子金”。起初这几种形状不同的货币各有一定的流通范围。到战国后期,随着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各地的钱币有趋向一致的倾向,直到后来秦始皇统一了货币。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城市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据后人估计,在战国时代,我国就有了四五百万的城市人口。我们的先辈通过不懈的努力,不仅有了数目众多、规模宏大的城市,而且创造了灿烂的城市文化。